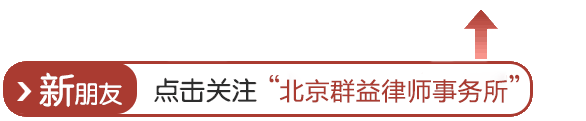
当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家庭痛苦并无本质差别时,仅因 “是否牟利” 的主观目的差异,就导致量刑从五年以下到死刑的天壤之别,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?一起看看今天的案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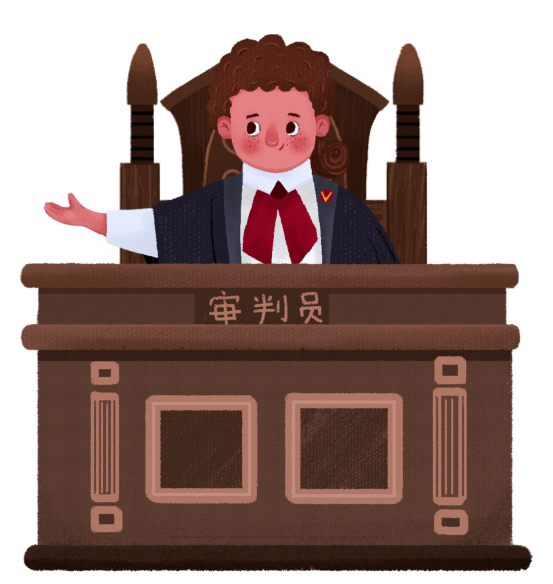
今日案例
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卓、符建涛被拐骗案,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飞龙有期徒刑5年,以包庇罪判处吴兆光有期徒刑2年。同时判令吴飞龙分别赔偿两个被害人家庭损失42万元。

对于这一判决结果,孙卓的父亲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女士均表示有很大的异议。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,只判5年”,这样的结果,对于关注此案件的公众而言,多少也有些疑惑,觉得判决量刑过轻。
那么,本案中法院对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,只判5年”的人贩子是判轻了吗?
群益普法
本案中,被害人没有上诉权,即便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,也只能向检察院申请抗诉。至于是否抗诉,决定权在检察院。
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,检察院抗诉的前提,是“第一审的判决、裁定确有错误”,其中包括事实不清、罪名错误、量刑畸轻畸重等。在本案中,比如: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起诉被告人,而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定罪;或者检察院量刑建议较重,而法院判决轻缓,检察院抗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
检察院起诉吴飞龙的罪名是拐骗儿童罪,对其量刑建议是5年有期徒刑,这也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。也就是说,一审法院对于检察院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“照单全收”,检察院似乎没有抗诉的理由。即便检察院抗诉,被害人和公众希望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愿望也难以实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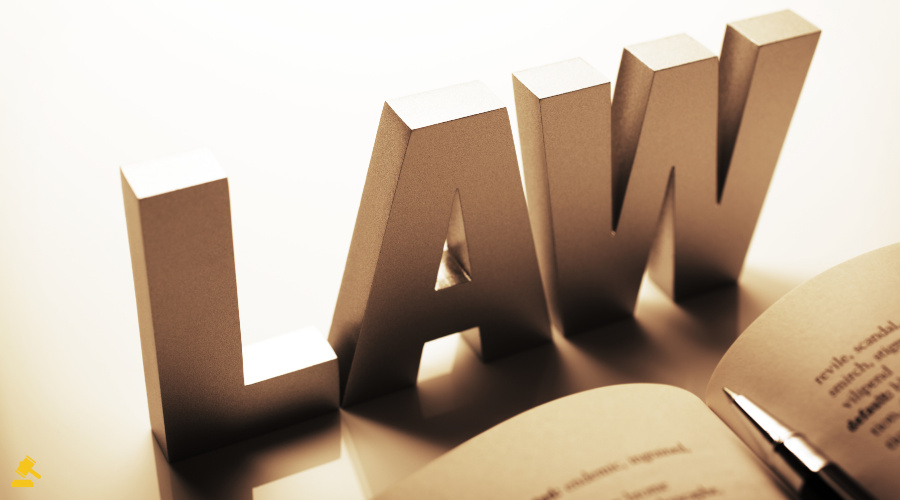
本案中,公安机关未能经过侦查取得被告人吴飞龙拐卖的事实及证据,因此,检察院只能以拐骗儿童罪提起公诉,法院对其定罪,被害人和公众对此感觉不公,这是证据的无奈,除非后续取得拐卖的证据。
对于检察院来说,即便在10日抗诉期内取得被告人吴飞龙拐卖的证据,也不宜因此抗诉,在二审程序中变更指控罪名。因为这样做,一旦被告人被定拐卖儿童罪,就相当于“一审终审”,被告人便失去了上诉的权利。正确做法是等到判决生效后,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判决。
本案之所以引起公众质疑,症结在于不同罪名在法定刑上的差别:拐骗儿童罪,最高判5年,而拐卖儿童罪,最少判5年,最高可判处死刑。“拐卖”和“拐骗”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同。构成拐骗儿童罪,没有特殊目的要求,实践中多是为了收养或役使;而拐卖儿童罪,则是出于贩卖牟利的目的。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动机、犯罪手段、犯罪目的、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的区别,对两罪在量刑上做区分是必要的,但就导致骨肉分离、给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带来极大精神痛苦的犯罪后果,两种犯罪并无不同。因此,对拐骗犯罪行为过于轻缓的刑罚无法起到震慑的作用。
因此,在今后的司法中,为避免“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”类似情况,立法机关不妨就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公众的疑虑,予以重视和考虑,提高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期。

诉说你的忧愁,群益帮您解忧
作者:北京群益律师事务所-吴宏斌律师
文中所有图片、视频,如无特殊说明,均来自互联网
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版权问题,请联系小编

